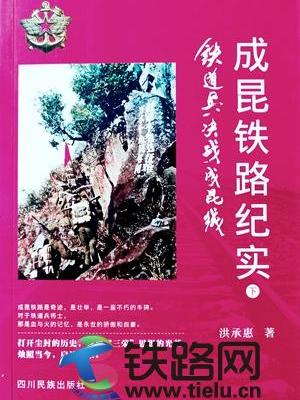暮色漫过键盘,茶雾在显示屏前晕开一阕朦胧的散文诗。指尖叩击的脆响荡开记忆深潭,那些蛰伏在钢轨褶皱里的光阴碎片,如道砟般簌簌滚落在二十六键方寸之间。
十七岁春汛漫过湘黔线时,我撞见一个枕木作韵脚的人。绿皮车厢摇晃着老工长的搪瓷缸,铁锈味的掌心摊开五等小站的值班日志。"看那晨昏线在轨缝跳舞",他教我辨认远方地平线处平仄相生的弧光。后来每趟巡检,弦线在我眼里都成了游走的七绝,道尺丈量出的轨距恰似工整的骈文。
文字原是钢轨豢养的精灵。春汛决堤的雨夜里,防洪桩在值班日志上疯狂生长,化作《六条汉子和一推危石》;夏蝉嘶鸣的午后,钢轨膨胀的呻吟被译成《小站人,扛起责任与大爱》。键盘成了跨时空的轨检车,把沪昆线岩英大弯道上的风笛声碾成铅字,载着老龙师傅三十年未寄的家书,驶向黔东南的层层梯田。
记得K554+400米护坡塌方那夜,暴雨将抢险号子浇铸成青铜诗行。应急灯摇晃的光晕中,师傅掌心血泡渗进砂浆:"新砌的挡墙是山河结痂的疤,咱们的道砟可是敷在光阴伤口的药。"检查锤敲击钢轨的脆响突然有了平仄,我蘸着泥浆在值班本上记下:此刻,文字不再是墨迹,而是撬动群山的道钉。
如今落地窗将往事折射成万花筒,那些散落在轨枕间的文字,早长成绵延千里的洋槐林。春絮是未及装订的诗稿,秋叶是飘落的句读,年轮里封存着百万吨乡愁与汽笛的和鸣。每当深夜伏案,总能听见车轮的铿锵在字词间隙游走——那是钢轨与文脉共震的节拍,是岁月馈赠的复调史诗。
四十三年光阴沉淀成键盘包浆,墨水瓶里悬浮着永不坠落的星辰。当最后一份文件归档为历史底稿,我仍在等待钢轨尽头的地平线涨潮。那些在轨缝中发芽的故事,终将以文字的形态,站成永恒的月台。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