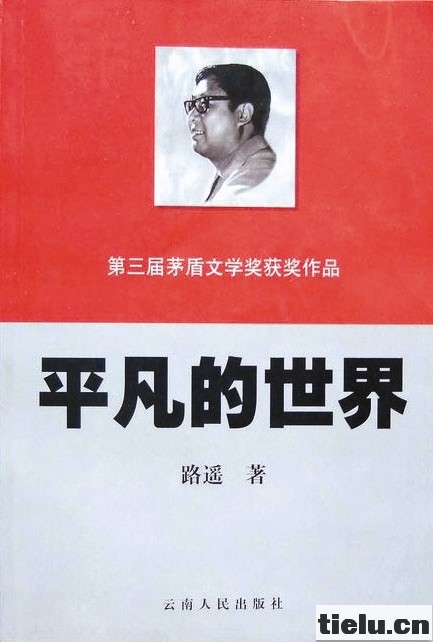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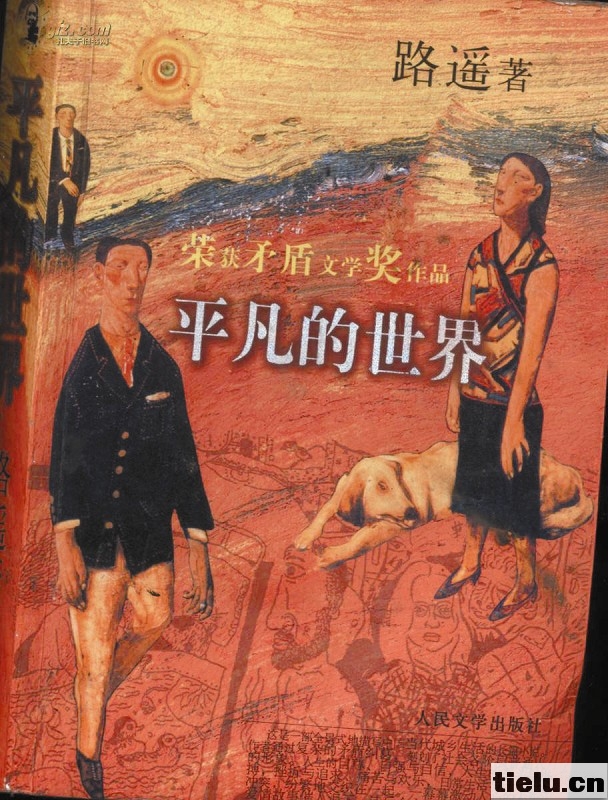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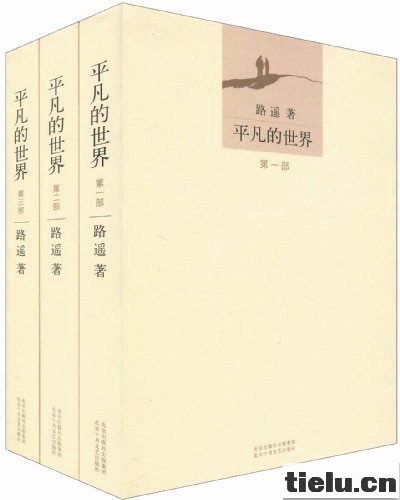
第一次读路遥 《平凡的世界》是在20岁出头的时候。那时我还年轻,心浮气躁的,吞枣子般把书翻了一遍。然而,作品中那群农村青年为寻找自己的幸福和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英雄式奋斗史和他们坚定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信念,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依然鼓舞着我去战胜困难。
20年了,路遥这部 《平凡的世界》不断再版,印数海量,并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和拥有独家网络版权的乐视网同步热播。为什么20年来这部小说生命力不衰,影响力越来越大,还如此火热?不仅因为这部史诗叙事小说中蕴含着高远的理想和深邃的思想,而且与作家路遥把一生都活在理想里,以 “身体还乡” “精神还乡”的创作姿态和 “把生命之弦拉到极限”的创作精神,完成三部六卷100万字的 《平凡的世界》密不可分,这也是我一直把这本小说当作励志书来读的重要原由。
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书写乡土历史生活的典型之作, 《平凡的世界》主要描写了从1975年到1985年10年间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历史发展。从构思到出版,路遥整整花掉了6年的时间,仅准备工作就花了3年。他阅读了100多部长篇小说,翻阅了10年间的 《人民日报》 《参考消息》 《陕西日报》 《延安报》。为获取灵感,他钻山林、下煤矿、进学校、睡窑洞、喝凉水,不止一次地跑到故乡的毛乌素沙漠里体验,也无数次在深夜里因写不出自己满意的文字而痛哭流涕。这种近乎 “自我折磨”的艺术创作活动,充分体现了路遥把高远理想当作自己生命的第一追求。如果没有深邃的历史理性、迎风而立的文化性格和博大的文学胸怀,这是万万做不到的。
路遥坚持 “历史书记官”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以 “朦胧诗” “实验小说” “寻根文学”为代表的写作潮流中, 《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当时不但没有得到文学界的认可,而且评论界也指责 “创作方法过于陈旧”,但路遥却逆风而上。在给友人的通信中,他这样明确自己的创作观念: “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细读 《平凡的世界》,路遥尽管熟悉农村,也熟悉农村改革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但他对改革的全局并不做简单评判,而是把孙少安、孙少平、田润叶、田晓霞等农村青年抛到这个复杂性里,让他们在这复杂性里迷惘、漂泊、痛苦,经受种种怀疑,历尽种种艰辛。反过来,这些人物的迷惘、怀疑和艰辛,又是环境复杂性的具体展现——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说,这些青年人受尽了生活的磨难,但他们始终带着一种追求理想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奋发图强地进行人生搏斗。他们顾不上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的生存条件,甚至要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具有一种“自我觉醒的改革意识”,以个人而非集体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路遥对这段历史做出的一个文学的、艺术的概括,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平凡的世界》告诉我们: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
小说体裁强调的思想性不同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思想性。它的思想性是与作家的生命情感体验、艺术直觉以及作品的思想价值融为一体的。越是伟大的作品,这种思想的融合度越高,而在这种融合中, 《平凡的世界》高远理想的生命力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一部具有理想情怀和思想深度的作品,绝不是昙花一现的瞬间景观,传之久远自在情理之中。正如路遥所说: “我们不应该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因为只有反映出了生活中真实的矛盾冲突,艺术作品的生命才会有不死的根。”
当前,文学艺术的理想情怀被弱化,乃至被边缘化。重建文学艺术的理想精神,承担起烛照国民精神的光荣使命,是这个时代对文学艺术的迫切要求。但愿 《平凡的世界》这颗 “茅盾文学奖”的耀眼明珠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