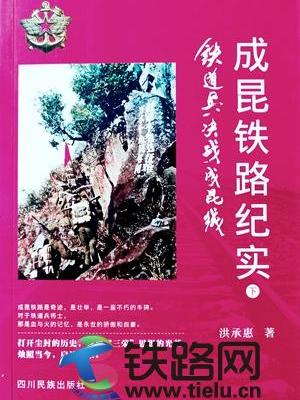钢轨在晨光中伸展成五线谱,青春是跳跃其上的音符——汽笛是它的强音,轮轨私语是它的弱拍。四十三年前那个揣着《拜伦诗集》走进工务段的少年不曾预见,岁月会把诗句锻打进道钉的螺纹,让散文生长在头灯明灭的间隙里。
安全帽系带在额头刻下年轮,却束不住目光追随列车撕开浓雾。那些被车轮带走的晨昏,最终都凝成显示器里流淌的星河,每个字节都浸着柴油的气息,在屏幕上铺就通往文学圣殿的枕木。检查锤惊起草尖露珠的清晨,钢笔也在日志本划出相似的轨迹,背包里两件"违禁品":《普希金诗逊的页边沾着机油,采访本扉页烙着钢轨印迹。
"拿着扳手的诗人"——工长的调侃里藏着真理。那些螺栓的扭矩系数,确实比十四行诗更讲究格律。深夜值班时,信号灯的红绿与屏幕蓝光调配成奇异的调色盘,当"区间闭塞"的电子音响起,突然顿悟:文字与列车同样需要精确的进路编排。
老扳手柄部的包浆是最诚实的编年史,记录着四十三个严冬与冻结螺栓的角力。而工具房最动人的秘密,是月光下扳手与钢笔的对话:金属的冷硬赋予文字筋骨,文字的柔软又让我触摸到钢铁的体温。那年水害抢修,泡胀的稿纸上晕开的何止墨水?更是文学梦与职业信仰的初次淬火。
暴雨中的钢轨如淬火长剑,线路工的身影是移动的铭文。当同事抱怨雨水灌进雨靴时,我正为发现"轨缝雨帘似流动琉璃"而雀跃——这篇观察后来被称作"技术员的浪漫主义",其实不过是铁路人的通感本能:早把内六角扳手当钢笔,钢轨作琴弦。
初雪覆盖的小站像奶油蛋糕,除雪的线路工是插在上面的蜡烛。当那张道岔除雪图片获奖时,老工友才理解:铁路文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实用与审美的黄金分割点,如同道砟既要托起万吨重量,又要留住晨露的晶莹。
如今教导年轻通讯员时,总让他们先触摸钢轨平面:"好的文字就该这样——经百万次摩擦仍从容。"他们不会发现,我电脑里永远同步更新的两个文件夹:《小站线路养护记录》和《未完成的铁路史诗》。
暮色中的站台,亮起的橘黄灯牌如落日碎片。远眺列车飞驰的剪影,终于明白人生恰似这些永动的车轮。曾经纠结的"铁饭碗与文学梦",原是一组并行的钢轨,在生命的地平线上延伸成永恒的平行线。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