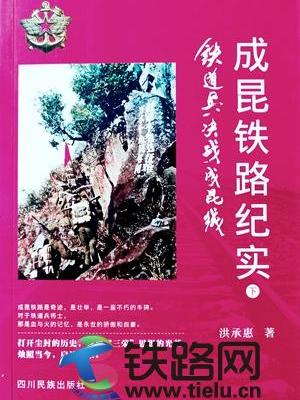朵拉图
图为朵拉图近照
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父母在另一个城市。记忆里,外婆就是母亲的含义,而母亲只是一个称呼。母亲是一个严厉的女人,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外婆家教训我。小学三年级的假期,我第一次来到父母家里。在部队大院里,一排平房的其中两间就是我们的家。到家的第一天是下午,父亲出差了,母亲坐在餐桌旁看着我,能看出她在努力让眼神温和起来。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她的眼里找到外婆的溺爱,我还是很怕她,坐在自己的小床上很拘谨,用简单的 “是”与 “不是”回答着她的问题,心里希望时间再快一些。其间,她几次去卧室,我竟然希望她别出来。有一次,她拿出一把用红红绿绿的彩色纸包的糖块,问我想吃吗?我居然忍着口水说不吃。又一次,她拿出几本图书,问我喜欢看书吗?我瞥了一眼,都是些小孩看的,白雪公主之类的童话故事,外婆给我讲过无数遍了,心里说我才不看那么幼稚的东西呢,同时我猜测卧室里到底还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母亲上班前把穿着红绳的家门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告诉我在餐桌上做作业,累了出去玩会儿,在家就在客厅玩,别去她的房间。母亲走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她的卧室。卧室的西北角靠着西墙和北墙放着一张大床,顺着东北角的东墙是一个竹子制作的书架,褐色的竹子上面布满了浅褐色的枣状斑点。那时我10岁,并不知道这种竹子名为湘妃竹,后来读到毛泽东的诗词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才知道有关湘妃竹的传说。书架共四层,每层都码满了书,书的上面盖着白色绣花的布。我为我的发现而开心。接下来,这一发现让我惊喜,南墙的窗子靠左边,右边靠墙放着一个硕大的黄色木质书架,木头粗糙,上色不均匀。整个书架被上下左右四块白色的绣花布像窗帘一样遮挡着。我兴奋地拉开下面的两个窗帘,数不清多少层、多少个隔断,上面堆满了书,很多书都泛黄了。我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本 《普希金诗集》,读到的第一首诗歌是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瞬间就被诗歌的美妙吸引了。紧挨着 《普希金诗集》的还有泰戈尔、海涅、雪莱等大家的作品。那一刻起,我开始了如饥似渴的阅读经历。这些书全都是繁体字,我怎么会在10岁发现这些书本的一瞬间,突然认识繁体字了,至今我还纳闷。最初我是胆战心惊地阅读,每一本读几篇立刻放回去,再读第二本,好像怕一本书在自己手上停留时间长就会被发现一样。偷着读了3天后,并没有被母亲发现。我胆大了,干脆坐在书架边的地上,一本看够了再换。我记忆最深的一本书是 《我们播种爱情》,那时, “爱情”这个词会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神秘。
在读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逊时,我发现了许多陌生的名字,阿尔维斯引用了他们的作品,如莎士比亚、雨果、拜伦、歌德……每读到一个名字,我就在书架上寻找他们的作品,每找到一本,我都像挖到宝藏一样欣喜。
假期很快就要过去了,母亲问哪天送我回外婆家?我很纠结,我想念外婆,归心似箭,可更想读那些书。当我说我想留下上学时,母亲眼中掩饰不住喜悦,陶醉在自以为两个月就可以让我依恋她的想象里,而我在那个晚上躺在单人小床上因为想外婆偷偷地哭了很久。到今天,我惊讶我可以在10岁时为了读书做出那样的选择,那时,我已经体验了生活中不得不选择取舍的残酷。每天我放学后,到母亲回来之前,都是我阅读的时间。那段时间里,书籍就是我的玩伴,宛如一个每天都换亮丽华服的洋娃娃一样,让我兴趣盎然,伴随我度过了离开外婆半年之久的时光。新学期一开始,我便转学回到了外婆身边。
我17岁时,已经进入上世纪80年代了,那时的中外名著竞相出版。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阅读,随心所欲地读自己喜欢的书,重读莎士比亚、泰戈尔等人的诗集,读了所有我可以买到或借到的中外名著。列夫·托尔斯泰在 《复活》里描述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聂赫留道夫公爵一次偶然的机会作为陪审员参加审理一个命案。从被冤枉的妓女马洛斯娃特别的眼神中认出了她曾经是他青年时代始乱终弃的卡秋莎。而卡秋莎在以后的艰辛生活中堕落成妓女马洛斯娃……聂赫留道夫因为卡秋莎的不肯原谅,不断地拷问自己的灵魂……最终他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双重复活。那个时期,我常因为读到一本好书而寻觅作者所有的作品,比如在读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后四处寻找茨威格的作品。
在一本西班牙小说里,我读到了令我震撼的细节。在法西斯的女囚监狱里,一个身体虚弱的女政治犯,决定替另一个被判死刑的女囚去死,因为那个女囚有一个孩子需要抚养。视死如归的女人,把人性的伟大演绎得如此完美。后来我在狄更斯的 《双城记》里看到了相似的情节,只不过这次是演绎了爱情的伟大与献身精神。这部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在揭露社会的矛盾与黑暗、深切同情底层人民的同时,描绘了超越现实与人性本质的凄美、伤感,动人的爱情故事,让读者为之动容,并铭刻心间。
那几年的阅读,让我充实了自己,看到了精彩的世界,并寻到灵魂相近的伴侣。出嫁时,我向母亲要的嫁妆是那个湘妃竹的书架,和我挑选的满满一书架书。婚房是老公单位的一间单身宿舍,但是那一架书让我感到富如宫廷。后来我们搬过多次家,房子越来越大,家具淘汰了一次又一次,可那个书架一直跟随我。今天,我卧室里的家具是整套的象牙白欧式家具,那个书架依然占据一席之地。
现在的我,早已步入中年,读书仿佛已经成为一种需要,尤其是在冬天,像张炜散文里描述的那样:在备感孤独的寒冷中,听到悬挂的冰凌跌落的脆响,听到风声,就更加渴望和求助于一种阅读……今天,我的阅读更像是一种习惯,陶醉在文字的海洋里,除了汲取养分,还有一种情不自禁,一种流连忘返。
系青岛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