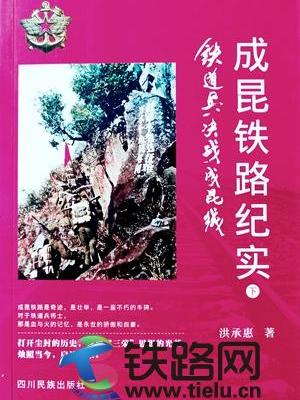若不是这次父亲病急如焚,我怎么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竟对父亲一无所知。
匆匆赶到病房的时候,父亲还在昏睡着。脸颊深陷,好像用力吸着双颊,颧骨分明,眉头紧蹙,额头的五线谱和眼角的纹路被岁月雕琢得深刻而久远,头发长而油腻,全身一股汗臭味。穿着灰白相间的病服,盖着白色略潮的被单,脚趾露在外面,双脚的大趾、二趾都已乌黑发青。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左手输着青霉素,右手打着安定。柜子旁边放着监测仪,除了血压低其余皆正常。
突然伴着“啊哟噫噫——呵”的一声叫喊,父亲面目狰狞双眉锁紧,脸上的沟壑愈加纵横,双臂用尽全身力气上举,拳头紧握,血管筋脉暴起,全身颤抖着,母亲急忙“啪、啪、啪、啪”有节奏地捶打着脊梁骨,姐姐拉着父亲的手说,爸,放松点,忍忍就好了。父亲挣扎了两分钟左右,疼痛才稍减,又平静地昏迷过去了。比起疼痛,倒宁愿昏睡。我轻轻喊了声,爸,爸,我回来了。我的右手拉着他的右手,左手抚摸着深锁的眉心,想要将这褶皱抚平,可似乎怎么也抚慰不了。父亲慢慢撩起脸皮,挤出一条缝,很快就闭上了。母亲说,二女儿回来了,醒醒别睡了。父亲再次撩开沉重而疲惫的眼帘,仿佛几十年间的沉瞌睡要在此时才能睡够,他微弱的声音和口型说,哦,回来了。接着意识又朦胧起来了。没过几分钟,又开始抽得前胸后背疼,声唤不已。
想来至少有十几年了,没有和父亲拉过手,没有端详过他的脸,没有一起肩并肩散步。唯一回家说得最多的就是,爸,吃饭了。因为他永远是最后一个坐到饭桌前。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手掌很硬、很糙,掌纹很粗很深,老茧磨得我掌心不舒服,手指明显变了形,微蜷,关节处粗大,指甲扁平,呈青灰色,总体看着很不协调。就是这双饱经风霜的大手,抚育了我们姐弟四人成年。
握着这双陌生的手,看着这张亲切的脸、这副瘦弱的躯干,突然间发现对父亲知之甚少。父亲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小,但并不因此而受宠。打小听话懂事、勤奋好学。17岁高考落榜,次年补习。据父亲讲,他正在学校上课,爷爷说奶奶病危,就空手回家被迫辍学。时日不长,奶奶病逝。自此父亲便开启了教师生涯。21岁与母亲相亲而婚。后迫于生计转政,走上小公务员之路,直至50岁退休。工作30年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听母亲讲,父亲常常把学生作业拿回家里来改直到深夜,经常在山区爆发滑坡、泥石流时默默值夜班。我也记得小时候常常看到父亲的“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先进党员”、“优秀干部”等等证书,那时候,证书上发烫的金字时刻鞭策着我们姐弟要好好学习,超越父亲。他从来没打过我,偶尔气急骂一两句,无非是因为儿时看电视太久或者睡懒觉之类的。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和父亲做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心灵上的沟通,甚至从来都没有汇报过我的思想、工作情况,只是一句“好着哩”敷衍了事。我也不知道父亲前半生都经历些什么苦难的事情,只从母亲嘴里知道父亲不易!
想到这些,我觉得自己愧为人女,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有爱却深埋心底,不曾表达也不曾回报。也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病魔,让我知道父亲于我们这个家、于我有多重要。
如果说母亲的爱像太阳的光芒,暖在心窝;那么父亲给予我的爱更像月亮的光辉,温婉而宁静,没有喧闹,甚至没有只言片语,只是背后默默的付出,于无声处滋润我的心田,于无形中潜移默化我的性格,照亮踽踽前行的路,不再彷徨,不再忧郁。
幸好,幸好有机会再爱。父亲,后半生让我来好好爱你吧。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